作者:佚名;来源:网络;时间:2023-03-16 10:31;浏览:604
上野千鹤子《15个小时的新娘》全文
在这世上存在四处打探他人隐私并将之当作八卦的卑鄙之人,而所谓“文春炮”便是其中之一。
在2月22日发行的《周刊文春》中登载了“单身教的教祖,上野千鹤子已经结婚”的文章,爆料了2年前去世的历史学家,色川大吉和上野是夫妻关系。文春不仅在没有向我进行过任何事实确认的情况下发表了文章(对方没有预约就找上门来取材,我当然拒绝了),文中甚至还有错误的部分,为了捍卫我自己,我不得不如此进行说明,这实在令人不快至极。
第一,我从来就不是所谓“单身教的教祖”之类的存在,也从未组建、发展过所谓的“单身教”,这是一个嘲讽性质的词。
第二,原本“入籍”这个词就是错的,正确的表述应该是“提交了结婚申请书”。不过既然都调查到了这一步,日期也该写上才对吧?我和色川先生的婚姻申请书于2021年9月6日在当地机关提出,而色川先生的死亡证明申请于次日9月7日提交。婚姻申请书提交后的凌晨三点,色川先生死亡。从提出婚姻申请开始,实质只有15小时的婚姻关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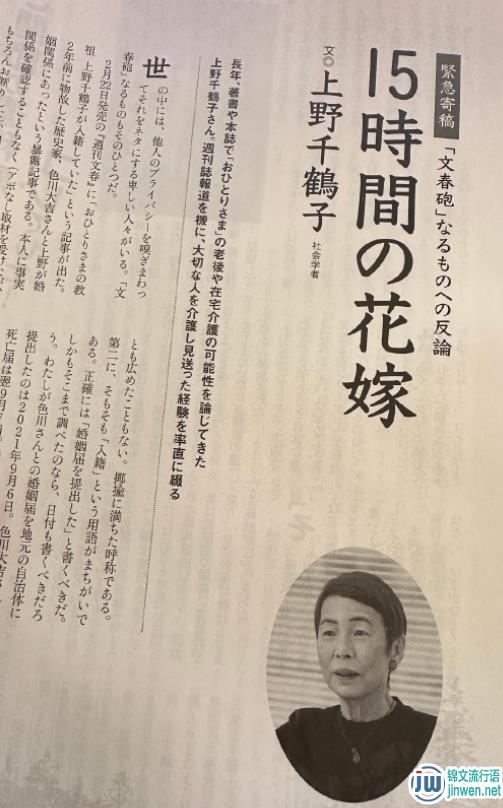
色川先生于96岁身故,在他八岳南麓的家里照顾他到最后的人确实是我。因为摔断大腿骨,色川先生已经不得不靠轮椅生活了三年。这期间还迎来了新冠。我从东京迁往自己山中的家“避难”,工作也基本转为线上。我工作的地方和色川先生的家属同一地界,我利用介护保险,成为了色川先生全面介护工作的关键人物。那期间,我一直在东京和八岳之间往返,但后来因为新冠,往返变得困难(应该指多次的紧急宣言),也就以此为契机,幸运地成为了可以在第一现场“介护”的人。
色川先生大我23岁,会在我之前去世也是意料之中。他离开他八王子市的家已经20多年,妻子也已经去世,只有自己独自生活,和儿子也是很少有机会相见的关系。色川先生需要介护,以及由我处理介护,色川的家人也都知情。
随着介护的长期化,衰亡也成了肉眼可见的过程。我和色川先生多次谈到他死后的事情,我(注:在法律上)完全是他关系外的人,连死亡证明申请书也没办法提交,到了紧要关头,入院或手术的同意书也没办法签字。也彻底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手续都以家族优先的事实。介护期间,色川先生的资产也是由我打理,预存金需要解约,在把银行账户挨着归总到一个账号时,银行工作人员问我“你们是什么关系?”,我回答说是“友人”,对方表示无法办理,直接打电话向色川先生进行了确认。还有更多数不清的麻烦事,因此想了很多,最终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日本这种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法律。有两个办法,要么是成为养子关系,要么成为婚姻关系。
成为养子的话,我在法律上就只能改姓色川。因为日本的养子缘组制度是为了家族的存续才存在的,哪怕对方只大你一天,年长的一方也是父母的一方(注:因此必须改姓)。而如果是婚姻关系,夫妻双方的姓必须统一为一个(注:日本的婚后夫妇同姓制度,但几乎没有冠妻姓的)。而我在色川死后还有长久的人生,为了让我之后不会面临不利,色川先生同意改姓为上野。是我改姓,还是色川先生改姓,在我还艰难选择时,色川先生已经先行签了两封文件(根据文春向“对继承问题很详细的律师”的取材内容,有几种情况是可以死后恢复原姓的,但我当时并不知晓)。在亲密的友人的见证下,2封色川先生已经签好的文件 (注:应该是指婚姻申请和改姓申请)就那样原封不动地放在我身边,而我依然在迷茫。
2021年夏天,色川先生已经无法吞咽固态食物,也连续五天没办法喝水了。黄疸进一步加重,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死兆。真的差点死掉。趁定期巡回来访的介护士来家时,我连忙驱车前往市役所,提交了结婚申请书。色川大吉也更名为上野大吉了。看到这个名字写在死亡证明申请书上,我感到一阵怃然。如果导入了“夫妻别姓制度”,事情也不至于发展成这样吧。我这一边因为没有改姓而避免了一切不利,如果是这样,那不改姓的一方确实难以理解改姓一方的不便和辛苦。而且,日本的法律如果不是家族主义的话,也不至于此。
真的从八岳南麓介护工作者们得到了很多照顾,色川先生似乎是这家公司的第一位顾客。色川先生是他们定期巡回短时间访问介护的对象,每天早中晚三次,无论风晴雨雪。如果没有他们,想必我是没办法维持在家介护工作的。也极大地体会到了介护保险的好处。清里也有提供访问诊疗的医院,那里的医生成了色川先生的主治医生。包括还接受了上门复健服务。大腿骨折的时候,色川先生拒绝了入院手术治疗,而选择在家修养。医生多次确认色川先生是否希望在家迎来最终时刻,色川先生也对此做出肯定的答复。明明没有做手术,但色川先生的恢复能力却是惊人的,能靠轮椅自己移动,也能自己上厕所。
色川先生的故乡有人来看望他,他把我介绍为:“这个人是介护的专家…”要这么说也没有错,不知道内情的人可能也会以为我是介护士。色川先生不仅头脑清晰,还具有相当的幽默感,“上野啊,现在是你实践理论的最中心处啊。”
色川先生向其他人介绍我时,最让我开心的一种是:这是我的亲友。山里的家附近的邻居大多是从城市移居过来的,因此维持着一种适当的距离感和成年人之间的关系。虽然也知道这是上野,那是色川,但“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?”这种问题一次也没有问过。
也受到访问介护士的诸多帮助。定期巡回介护有个选项是随时呼叫。拿着看护士资格证做着访问介护的N女士一直告诉我说有任何困难随时可以找她。只有一次,色川先生临终前的某个深夜,我因为色川先生的呻吟而醒过来,通宵守在他身边。因为自己无法为色川先生做任何事情而深感无力,捂着脸一直痛哭。就这样下去的话自己没办法支撑,谁能来帮帮我,这样想着,在深夜拨通了N的电话。她对我说:“上野,你按照自己写过的那样为色川先生介护了呢。”如释重负。
色川先生去世以后,多家媒体来找我写稿子或是取材,我全部拒绝了,因为还无法整理好悲伤的心情,也不想贩卖自己的隐私。
半年后,仰慕色川先生的人们召开了追悼会,在他们的邀请下,我无法回绝,写了一篇小短文,以《谢谢你,色川先生》为题,收录在《追悼民众史的狼烟,色川大吉》一书中。就是读到那篇文章,记者们才嗅着味道找过来的吧。本来也没打算隐藏,只是一开始就没有一定要公开的理由。知道的人都知道。我那些体面的朋友们也断不是贩卖友人隐私的卑鄙小人。如果有第三方散布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故事,还不如由当事人的我来亲自讲述,这也是我写这篇稿子的原因。